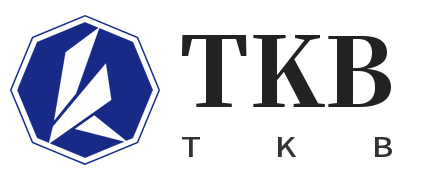根骨为梁
世人常道“人最大的依靠是自己”,听来激昂如战鼓,却隐约透着一丝孤绝的寒。若将这“自己”仅仅理解为现时此刻的意志与体力,便如同只仰仗一株无根之木去抵御八方风雨,终究是危殆的。真正的“自己”,并非凭空而来、凭空而立的孤岛;它是一座恢宏的建筑,其最深沉、最不可摧的依靠,乃是深埋于时间与记忆之下的**根基**——那些看似由他人赋予,实则已与我们骨血交融的文化印记与精神传承。唯有当这根基深固,个体生命的梁柱方能岿然挺立。
所谓“依靠自己”,首先意味着精神坐标的自我确立。这坐标的刻度,却非天生地设,而来自文明长河的涓滴灌注。孔子栖惶于陈蔡之间,从者病,莫能兴,他依然弦歌不辍,坦然自问:“吾道非邪?吾何为于此?”那份在绝境中对“道”的持守与自信,其力量源头,并非一时血气,正是他深深浸润其中、“述而不作”的周文礼乐。那是一个更宏大、更悠久的价值系统在他生命中的内化与回响。屈原行吟江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,却发出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铿锵之音。他所善所守的“心”,是楚地香草美人的瑰丽神话,是上古圣王“遵道而得路”的政治理想。他的孤傲与自持,正是以整个楚文化乃至华夏信史的积淀为底色。他们的“自己”,是文明根系上开出的最倔强也最灿烂的花。
进而论之,人格的独立与完整,更需要一种内在秩序的构建。这秩序的蓝本,往往铭刻在那些早已逝去的先哲身影之中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那份与自然造化冥合的恬然自适,何尝不是庄周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哲学在具体生命中的实践?他“依靠”自己,选择了退隐,而这选择背后的精神支撑与价值评判体系——对自然真趣的珍视,对官场羁縻的疏离——早已在老庄思想的汪洋中沐浴成型。苏东坡历经乌台诗案,宦海沉浮,晚年贬谪儋州,犹能旷达吟咏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他赖以渡过劫波的“自己”,是一颗被儒家的担当、道家的超脱、佛家的空观反复淬炼过的“亦一亦非”的玲珑心。这些内在秩序的建立,使他们得以在外部世界的惊涛骇浪中,保有一方安宁而自足的精神舱室。
当生命行至绝处,面临存在性危机的深渊时,那种看似最孤独、最本真的“自我依靠”,其深处激荡的,往往是整个文明血脉的澎湃。文天祥兵败被执,幽于暗室,在《正气歌》中历数“时穷节乃见”的忠烈先贤: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……”他将自己置于一条由历史英魂铸就的璀璨星河之中,个人的生死抉择,于是接通了亘古的长存正气。他所依靠的,是那个由史册、典范与信念所凝聚的、超越个体存亡的“大我”。戊戌变法失败,谭嗣同慷慨赴死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这决绝的“自”,分明承载着对国族未来悲壮的期待,是儒家“杀身成仁”的古老训诫在时代裂变中的辉煌回响。此刻,“自己”已成为一种精神的火炬,其所燃烧的,是文明薪传中最炽热的火种。
由此观之,“人最大的依靠是自己”这一命题的真谛,并非倡导一种原子化的孤立与傲慢。恰恰相反,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:**个体生命最强大的自立,正源于最无私的传承;最独特的创造,往往是对最深广传统的呼应**。那只“自己”的舟楫,之所以能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,是因为它的龙骨,由千年文明的精魂所锻铸;它的帆索,与人类精神星空的坐标紧密相连。当我们说“依靠自己”时,我们依靠的,是那个已将山河岁月、古圣先贤之精魄化为自身筋骨的、更辽阔、更深厚的“自己”。这自己,有根有源,故而能顶天立地;这依靠,连通古今,所以可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