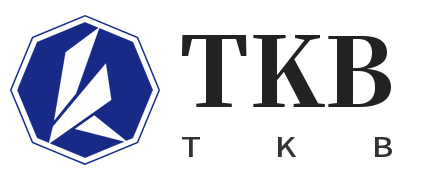## 有你很好,没你也行
水仙花的香气是忽然漫上来的。我正伏案,被这突如其来的清冽一惊,抬眼望去,书房角落里,母亲前日带来的那盆水仙,不知何时已悄然盛放。我搁下笔,在氤氲的香气里,竟有些怔忡。那白瓣黄蕊的小花,静默地立在青瓷浅盆中,底下是浑圆温润的卵石,清水刚没过根茎。它的存在如此安静,几乎要被忽略;可它的香气,却又如此不容分说,宣告着生命的完成。这像极了生命里某些人与事的注脚:存在时如静水深流,缺席时,那空出的位置却自有风来填补。
我于是想起林先生。他是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,个子清瘦,常年穿洗得发白的青灰色中山装,袖口有些磨损。他讲课声音不高,讲到动情处,比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或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,眼神会飘向窗外遥远的虚空,仿佛那里真有一个可供灵魂栖居的南山,或是一片无垠的秋水。那时的我们,懵懂顽劣,多半只觉他迂阔。他常在放学后,留几个对文字稍有感触的学生,从泛黄的书箱底,抽出他手抄的诗词残本,用修长的手指点着某个字,说它的古义,说它背后的山河岁月。那情状,不像传授,倒像一种郑重的托付。阳光穿过老槐树的枝叶,在他花白的鬓角跳跃。我们似懂非懂地听着,心却像被什么清凉而柔软的东西,很轻地拂了一下。
后来,毕业,离散,人如飘蓬卷入各自的江湖。激烈的竞争,现实的磋磨,少年时被诗书浸润过的心,很快结了一层硬壳。林先生和他那些“无用”的诗词,便像褪色的旧照片,被压在了记忆箱箧的最底层。许多年里,我几乎不曾想起他。我学会了另一种语言,一种关乎效率、逻辑与结果的语言,并凭借它,在都市的经纬线上,为自己谋得了一个还算稳当的坐标。没有林先生那些“悠然”与“秋水”的世界,运转得似乎更为迅捷、清晰。我以为,那便是成长的全部。
直到某个加完班的深夜,我独自驾车回家。高架桥两侧是璀璨而无机质的楼宇灯光,流线般划过车窗。车内电台流淌着嘈杂的流行乐,我却感到一种彻骨的疲惫与空旷。那一刻,毫无征兆地,一句诗撞进心里:“此身如传舍,何处是吾乡?” 我猛然刹住思维的惯性。这不是林先生当年在某个同样燥热的夏日午后,喃喃念过的句子么?那时只觉音韵苍凉,不解其味。此刻,在这钢铁洪流的夹缝中,在肉身与灵魂皆如旅店过客的漂泊感里,那九个字像一把沉寂多年的钥匙,“咔哒”一声,开启了一扇通往更深旷野的门。原来,那些看似被遗忘的、被“没用”的,并未消失。它们沉潜着,像深潭底的卵石,等待某一刻天光云影的垂顾,或某一缕特定频率的声波,与之共振,发出属于自己的、沉浑的回响。
林先生早已退休,音讯杳然。他的“缺席”是确凿的。我的生活轨迹,从任何实际层面看,都未曾因这缺席而停滞或紊乱。我依然朝九晚五,应对琐务,规划人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没你也行”。然而,从那夜之后,某些东西起了变化。经过街心见银杏黄了,不再是单纯的视觉信息,会想起“人间草木深”;与人争执后愤懑难平,心底会浮起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的宽谅可能;甚至在最为得意的时刻,也会警觉“高处不胜寒”的寒意。林先生不曾教给我任何处世技巧或生存技能,但他无意间,在我生命的底色里,滴入了数滴不为实用的、清亮的颜料。它们平日隐匿,却在某些独对的时刻,泅染开来,调和了现实过于坚硬的线条,让我在“非如此不可”的生存逻辑之外,瞥见了“也可以那样”的生命境界。
这大约便是“有你很好”的真意。那“好”,并非雪中送炭的必需,而是锦上添花的丰盈;不是支柱之于大厦,而是星辰之于夜空——夜空自有其浩瀚苍茫,但有了星辰的缀饰,旅人才在无边的跋涉中,望见了诗意与方向。一个人的到来,一份缘分的赐予,其意义或许正在于此:他(它)并非要来填补你生命的空缺,因为完整的生命本该自足;他(它)是来为你已然自足的生命,打开一扇新的窗户,让你看见原本就存在、却被你忽略的风景。他的存在,是一种珍贵的“附加”;而他的离去,带走的也只是“附加”,而非你生命的根基。那扇他推开的窗,却从此开着,风可以进来,光可以进来,你望向世界的目光,也因此多了一个温柔的维度。
窗台上的水仙,开得愈发蓬勃了。它的花期不过十数日,然后便会凋零,重归静默。但我知道,明年此时,或许不再是这株,但总会有新的生命在清水白石间绽放。它的香气会再次提醒我:有些美好,不依赖于永恒的占有,而在于瞬间的照见与长久的滋养;有些人的意义,不在于他是否始终在场,而在于他曾为你开启过一个世界,而那个世界,从此便成了你的一部分。
有你,生命多了一重山水清音;没你,我的天地依旧完整,只是那山水清音,已化作心底不绝的回响,在我自己的江湖里,细雨微风,润物无声。这便是生命赠予我们的一份从容:不执于有,不惧于无,在聚散之间,修得一颗既能深情寄托、又能安然独立的平常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