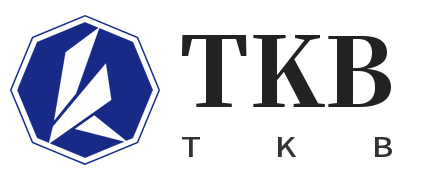## 浮尘下的棋局
这间临终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刻薄气味。七十五岁的陈默躺在白得刺眼的床单上,手上插满维持生命的管线,像一株被过度修剪的老树。他看向窗外梧桐光秃的枝桠,视线又落回床头柜——那里安静躺着一副褪色的木头象棋。
“我下了一辈子棋,”他忽然开口,声音沙哑得像风穿过枯叶,“赢过,输过,被人夸过天才,也被人笑过顽固。但我从没后悔。”
邻床新来的病友是个中年男人,因车祸截肢,终日沉默。听到陈默的话,他眼珠动了动,终究没有回应。
陈默并不在意。他让护工扶他半坐起来,颤巍巍摆开棋盘。红黑两色棋子磨损得厉害,尤其是那枚“帅”,侧面有道深深的裂痕。
“看见这道裂了吗?”陈默的手指拂过木纹,“1966年留下的。”
那年他十七岁,是省象棋队最年轻的选手。教练说他棋风“有古风”,像《橘中秘》里走出来的棋手。少年陈默的世界只有楚河汉界,直到那个闷热的下午,一群手臂缠红布的人冲进训练室。
“封资修的玩意儿!”带头的青年一把掀翻棋桌。檀木棋子滚落一地,有人抬起脚——
“别踩!”陈默扑过去,护住离他最近的那枚帅。军靴重重落下,他听见自己指骨碎裂的声音,也听见木头开裂的轻响。在谩骂与嘲笑声中,他蜷缩着,用没受伤的左手把那枚帅紧紧攥在手心。
“后来呢?”邻床的男人突然问。
“后来我去插队了。”陈默说,“行李里只有两样东西:衣服,和这副修不好的棋。”
他去了北大荒。冬夜漫长,油灯如豆,同屋的知青们打牌、想家、唉声叹气。陈默在炕桌上摆开棋,自己跟自己下。有人凑过来看两眼,摇摇头走开:“陈默,你这棋下得再好,能当工分吗?”
他沉默地移动棋子。炮八平五,马二进三。在虚拟的厮杀中,他忘记了冻裂的虎口、酸痛的腰背,忘记了回城的希望像远星一样渺茫。棋局是他唯一能掌控的疆域。
1977年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,陈默已经二十八岁。知青点炸了锅,所有人翻出蒙尘的课本。陈默也报了名,但复习到第三天,他默默收起课本,重新摆开了棋。
“你疯了?”好友夺他的棋子,“考上大学就能回城!”
陈默夺回那枚有裂痕的帅:“我下棋的手,拿不了笔了。”
不是不能,是不愿。那双在冬夜里反复摆棋的手,指节粗大,布满老茧,早已习惯了触摸棋子的温度。更重要的是,他忽然看清了——棋盘之外的世界有太多他无法理解的规则,而楚河汉界之内,他是自己的王。
病房里只剩下仪器规律的滴答声。陈默摆好最后一枚棋子,抬头看向窗外:“我这辈子,没拿过全国冠军,没教出大名鼎鼎的徒弟,退休前只是个少年宫的象棋老师。很多人说我浪费了天赋。”
他停顿了很久,久到护工以为他睡着了。
“可是啊,”陈默的声音轻得像叹息,“每天早上醒来,我知道我要去哪里、做什么。我给那些孩子讲棋理,看他们眼睛发亮的样子,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。我写了三本象棋入门书,卖得不好,但有个孩子写信来说,他因为我的书爱上了象棋。”
邻床的男人转过头来,第一次认真看陈默的脸。那张布满老年斑的脸上,有一种奇异的平静。
“遗憾?”陈默笑了,皱纹舒展开来,“该遗憾的不是我。是那些一辈子没找到自己‘棋局’的人,是那些在别人划定的战场上疲于奔命的人。我选择了我的棋盘,并且每一步都走得认真。将军——”
他移动棋子,完成了一个人对抗虚无的收官。
男人忽然说:“能教我下棋吗?”
陈默的眼睛亮了一下。他把棋盘转向邻床:“来,我们先认棋子。这是帅,它最重要,也最脆弱,所以你要用所有棋子保护它……就像保护你心里最不能丢的东西。”
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,给棋子镀上金边。那枚有裂痕的帅立在棋盘中央,裂缝里积着七十年的光阴,像一条金色的河。
陈默指导着男人走出第一步棋。在这个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房间里,在生命最后的刻度上,他依然坐在自己的棋盘前。窗外梧桐的枯枝映在棋盘上,像一幅写意画。他想起教练多年前的话:“陈默,你的棋有古风。”
原来古风不是招式,是明知世事如棋、人人皆欲为棋手时,甘愿留在自己的棋局里,做一枚有裂痕却永不更换的棋子。
仪器发出平缓的鸣响。陈默闭上眼睛,手里还捏着一枚棋子。他勇敢过,在军靴落下时伸出手;他努力过,在荒原冬夜里自己与自己厮杀。现在,他可以平静地离开这片经营了一生的疆域。
该遗憾的不该是他。因为真正的遗憾,从来不是输掉游戏,而是从未真正坐上棋桌,用全部的生命下一盘属于自己的棋。
棋盘上,那枚有裂痕的帅静静屹立。裂缝深处,光阴如金,沉默如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