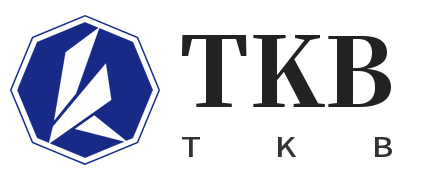## 见山记
夜半读《五灯会元》,忽见一句:“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,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。及至后来,亲见知识,有个入处,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。而今得个休歇处,依前见山只是山,见水只是水。”青灯之下,墨字如蚁,竟簌簌而动,爬满了眼前的白纸。我推开窗,想寻一片清寂,目光却被远处一脉黢黑的、沉默的轮廓攫住了——那是夜里的山。
这便是第一重了:见山是山。于我,这山是故乡的,有名字的。名是“云暮”,暮色与云气的孩子。儿时,它是我全部的地理与神话。阳面的坡种着祖父的茶,阴面的谷藏着外婆讲的、专吃梦的貘。山的线条,是每日睁开眼就望见的、摇篮曲般的起伏;山的声响,是清明时采茶歌的脆,是深秋里松涛的沉。它稳固如家门前青石门槛,任我趴着,将下巴磕在上面,看日头怎样给它镀金,又怎样把金子熔化成紫黑的铁。那时山是坐标,是背景,是伸手可触的实在,是“这个”。我从未想过山“是”什么,因为它就是它自身,圆满自足,像我呼出的第一口气那般天然,不容置疑。
离乡那年,火车吭哧着将“云暮”缩成窗玻璃上一个渐远的墨点。书上说,那墨点不过是地壳运动的褶皱,是岩层、植被与气候的偶然聚合。地质学、生态学、测绘学的术语如漫天冰雹,将童年那座温润的神龛砸得坑洼斑驳。后来我走过许多真正的名山,黄山的奇、华山的险,在它们的磅礴面前,“云暮”缩水成地图上一个无足轻重的等高线圈。我曾蹲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,看一方来自“云暮”同类山脉的、十几亿年前的砾岩,标签上的数字冰冷如手术刀。那一刻,我心里那座具体的山,确乎“不是山”了。它被概念肢解,被比较矮化,被知识抽象为一堆待分析的“对象”。我见它不再是故土,而是沉积年代、植被类型、开发价值。我与山之间,隔了一层名为“理性”的毛玻璃,清晰,却冰凉。这是第二重:见山不是山。人在这里,获得了一种剥离的清醒,也领受了一份飘萍的伶仃。
此番隔窗望夜山,却有些异样。离乡已久,关于“云暮”的具体记忆,譬如某条小径的走向,某处泉眼的滋味,早已漫漶不清。那些曾用以解构它的庞杂知识,也如潮水般退去,留下一片空寂的沙滩。剩下的,唯有一团浑然的、关于“山”的“意象”。它没有名字,没有海拔,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沉重,更饱满。我忽然觉得,童年那座具体的“云暮山”,与后来那堆抽象的“山的概念”,都像是为了抵达今夜这片“空寂”而必经的渡筏。
此山非彼山。它不再是私人的乡愁寄托,也不再是公共的科学标本。它悄然脱落了所有附加的意义与功能,还原为存在本身那巨大而沉默的在场。我见其黑,黑得如此丰饶,吞噬星光却内蕴洪荒;我感其静,静得如此轰鸣,耳中竟响起宇宙诞生前的岑寂。这静与黑,并非“无”,而是淘洗尽砂砾后留下的纯金般的“有”。唐代禅师青原惟信在说完那三重境界后,想必也曾面对这样一座山。他所“依前”见到的山,绝非简单地回到懵懂,那“只是”二字里,有千帆过尽的确认,有妄念止息的安然。仿佛宇宙洪荒,只为了成就此刻窗前这一片剪影的浑沦。
古人云“仁者乐山”,乐其静而寿。我非仁者,今夜却仿佛触及了那“静”的源头。这山在,一直便在,是我的“看”经历了尘埃与洗涤。从“是”到“不是”,是人在尘世中必然的出走与迷失;而从那“不是”再度确认的“还是”,或许已非归来,而是登临。登临到一个原初的、物我未分的点,在那里,看见即是确认,存在无需言诠。
远处,城市最后的夜光给山脊线镶上一道极淡的、银灰色的边,像一句即将被黑暗吞没的偈语。我关上窗,那浑然的山的意象,却已留在屋里,比一切实物更具体,比一切概念更真实。它不再是我故乡的坐标,而是我灵魂里,一块终于寻获的、压舱的石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