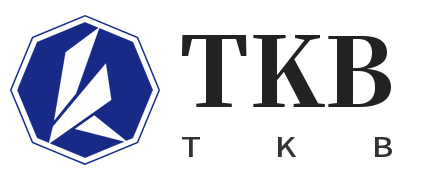## 虚舟记:云深不知处
世人说道家,总爱提“道法自然”,提“清静无为”。仿佛成了逍遥闲人,便可自称老庄门下。我初时亦作此想,直至那年在川西峡谷,于云雾深处与一老者对坐半日,方窥见这“追随”二字,是何等沉重而轻盈的虚舟。
那是个秋日清晨,峡谷为白雾所噬。山径石阶湿滑如鱼脊,两侧古木滴着隔夜的寒露。我欲寻一古观,却迷在雾阵里。正彷徨时,见前方崖边磐石上,有一青衫老者垂足而坐,身侧放一竹篓。雾从他须发间流过,又从袖口逸出,人竟似与云雾同质,静到极处,反生出一种流动的气象。
我近前,见他篓中尽是碎石,大小不一,棱角尚存。他一块块取出,并非赏玩,而是朝身后深谷信手抛去。石头落处,无声无息,尽被云海吞没。这动作单调重复,他却做得极专注,如行仪轨。我忍不住问:“老丈,这是做什么?”
他手上未停,只道:“听见了么?”
我侧耳,只有满山寂静,连鸟鸣也无。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他微微一笑,又抛出一块:“对了。这便是‘无’。”
这话玄虚,我却似被定住,在他身旁石上坐下。他言说极简,如他抛石的动作。从山谷开发,炸山取石,机器轰鸣数年,如今停工,留下一地狼藉碎石,如大地的痂。他晨昏至此,将碎石还于谷中。“不是清理,”他纠正我,“是‘复归’。”不为整洁观瞻,只为让石头回到它该在的“无”里去。
我心中一震。我读过百遍《道德经》,“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”字字认得,却在此刻,才觉有血有肉。他手起石落,是在践行最朴素的“复归”。这动作里,没有对抗开发的愤怒,没有环保的优越,甚至没有“我在做好事”的念头。只是看着“有”(碎石)生于不该生之处,便助其归于“无”(深谷)。动机纯粹如露水从叶尖坠落,不为什么,只是时辰到了,地心引了。
“这要抛到几时?”我问。
“抛到无石可抛,或我无力再抛时。”
“若永远抛不完呢?”
“那便永远抛下去。”他语气平常,如说吃饭饮水,“道者,万物之奥。善人之宝,不善人之所保。它不在乎做完做不完,只在做或不做。”
雾渐薄,阳光如金针探下,在他肩上绣出光斑。我帮他递石,触手冰冷粗粝。每块石头形状、重量皆不同。有些尖锐扎手,有些圆钝沉重。他接过去,并无二致地抛下,仿佛在抹平造物主无意或有意留下的皱褶。这重复里,有种近乎禅定的力量,却又比禅定多了份与天地共呼吸的韵律。
我忽然了悟,自己多年来自诩的“仰慕”与“追随”,是何等苍白。我收集各种版本的《庄子》,热衷于谈论“坐忘”“心斋”,在社交网络引用“上善若水”,以此构筑一个清雅脱俗的身份幻象。但这身份,与真实的生活、与脚下这片受伤的土地有何关联?我的“道”,是书房里的装饰,是言谈间的香料;而他的“道”,是手掌上的泥垢,是日复一日无声的“复归”。
临别时,雾已散尽,深谷幽翠,望不见底。他竹篓尚有小半碎石。我问:“明日还来么?”
“天若无雨,便来。”
“敢问老丈修持何观?”
他第一次露出略显讶异的神色,摇摇头:“我不居观。家在山下村里。种两亩菜,采些草药。此事,”他指指竹篓,“与采药无异,都是本分。”
我沿原路下山,双腿沉重如灌铅。回望那崖石,已无人影,唯余白云空悠悠。方才一切,恍然一梦。但那竹篓的触感,石头的重量,抛落时的弧线,却比任何经卷上的字句更真实地烙在手里、心里。
我从此不再轻言“我是道家思想的追随者”。这称号太沉重,它意味着你可能需要将一生,投入一件看不见尽头、算不出功德、甚至无人知晓的“复归”之事中去;这称号又太轻盈,它让你卸下“必须改变世界”的巨担,只是日复一日,如那老者,如溪边运石填海的精卫,完成当下最本分、最自然的一个动作。
云深不知处。那“不知”,并非迷路的茫然,而是了悟后的谦卑——我终于承认自己并不确知“道”的全貌,只知它不在玄谈中,而在每一次,将一块多余的石头,默默交还给深谷的刹那。那刹那,万籁俱寂,我听见了“无”的声音,那正是天地之心在搏动。而我,终于不再是一个旁观的仰慕者,开始学习做一个无声的、长久的参与者,在这永不停息的“复归”之流里,做一粒微尘,一片落叶,一块正在寻找其“无”的石头。